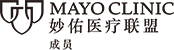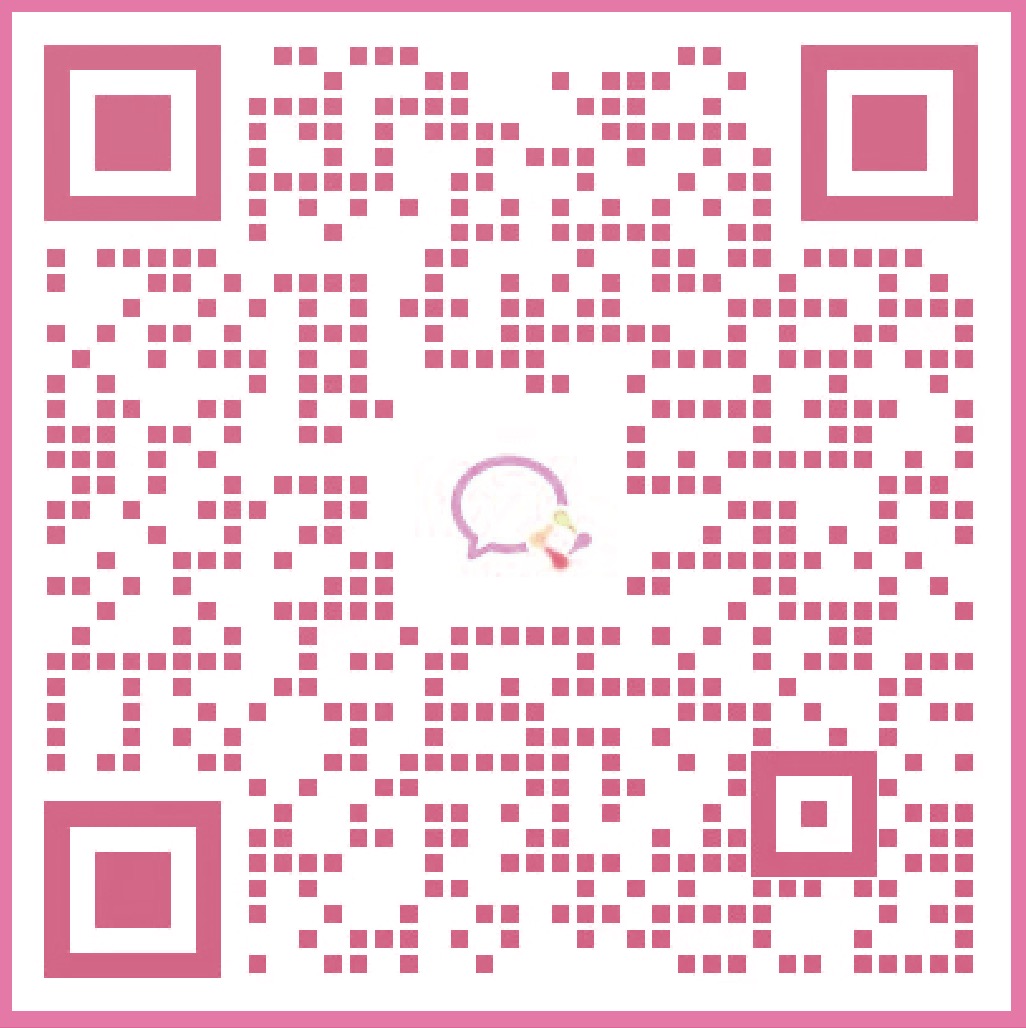佗曰:“大王頭腦疼痛,因患風(fēng)而起。病根在腦袋中,風(fēng)涎不能出,枉服湯藥,不可治療。某有一法:先飲麻肺湯,然后用利斧砍開腦袋,取出風(fēng)涎,方可除根。”
操大怒曰:“汝要?dú)⒐乱 ?
佗曰:“大王曾聞關(guān)公中毒箭,傷其右臂,某刮骨療毒,關(guān)公略無懼色;今大王小可之疾,何多疑焉?”
操曰:“臂痛可刮,腦袋安可砍開?汝必與關(guān)公情熟,乘此機(jī)會(huì),欲報(bào)仇耳!”
——《三國(guó)演義》第78回
孟德若在當(dāng)世,便知腦袋也能“開”,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(huán)就是麻醉。
西安國(guó)際醫(yī)學(xué)中心醫(yī)院麻醉手術(shù)中心副主任丁倩潛心技術(shù),致力于為患者提供安全、有效的麻醉,保證手術(shù)順利開展,為生命健康保駕護(hù)航。

丁倩
麻醉手術(shù)中心副主任
麻醉學(xué)博士、副主任醫(yī)師
陜西省醫(yī)學(xué)會(huì)麻醉學(xué)專業(yè)委員會(huì)青年委員會(huì)副主任委員
陜西省非公立醫(yī)療機(jī)構(gòu)協(xié)會(huì)麻醉醫(yī)學(xué)專委會(huì)常委、秘書
中國(guó)藥理學(xué)會(huì)麻醉藥理學(xué)專委會(huì)青年委員會(huì)副主任委員
中國(guó)心胸血管麻醉學(xué)會(huì)非心臟手術(shù)麻醉分會(huì)常委
中國(guó)非公立醫(yī)療機(jī)構(gòu)協(xié)會(huì)麻醉專業(yè)委員會(huì)委員
擅長(zhǎng)氣道手術(shù)麻醉,高齡、嬰幼兒及危重癥患者麻醉。
01初見醫(yī)學(xué)——是不是入錯(cuò)行了
“我們小時(shí)候西安風(fēng)沙特別大,上中學(xué)的時(shí)候刮沙塵暴,特別明顯,那時(shí)候國(guó)家也大力宣傳,講三北防護(hù)林,我當(dāng)時(shí)就覺得做這個(gè)事挺有意義的,后來也想學(xué)法律。但家里不是很支持。”胳膊拗不過大腿,丁倩最終遵從了父母的意見,學(xué)醫(yī)。
99年高考,丁倩的分?jǐn)?shù)基本打開了“任意門”,綜合考慮后選擇了第四軍醫(yī)大學(xué)臨床醫(yī)學(xué)七年制本碩連讀。
“一接觸醫(yī)學(xué),我覺得我選錯(cuò)行業(yè)了。”丁倩回憶自己和醫(yī)學(xué)的初次見面。“因?yàn)槲矣洃浟Σ皇呛芎茫铋_始接觸就是解剖,完全背不過。我一直是理科的思維,要搞明白為什么,但醫(yī)學(xué)很多東西必須死記硬背。”丁倩初進(jìn)醫(yī)學(xué)大門就碰上一座“大山”。
白天時(shí)間不夠用,那就晚上繼續(xù)!學(xué)員宿舍晚上10點(diǎn)熄燈,丁倩就在走廊里,一個(gè)大板凳、一個(gè)小板凳,繼續(xù)啃書。走廊里夏熱冬冷,燈泡的瓦數(shù)也越換越大,丁倩就這么堅(jiān)持下來,拿下解剖、藥理一個(gè)個(gè)“山頭”。
丁倩所在的七年制本碩連讀,如果出現(xiàn)兩門課成績(jī)70分以下,或是一門不及格,就會(huì)被淘汰到5年制本科。“那個(gè)時(shí)候?qū)W習(xí)壓力特別大,小伙伴們都特別刻苦。”丁倩所在區(qū)隊(duì)的36名學(xué)員,本科畢業(yè)時(shí)就淘汰了8個(gè)。

等到學(xué)臨床時(shí),丁倩覺得阻力小了很多,進(jìn)入了自己習(xí)慣的部分邏輯性思維,學(xué)習(xí)效率很高。
本科第3年過半,根據(jù)學(xué)校安排,丁倩開始一年半的見、實(shí)習(xí)階段。眼科、耳鼻喉科、胸外、普外、麻醉、心內(nèi)、消化、呼吸,神經(jīng)內(nèi)科、內(nèi)分泌等,丁倩轉(zhuǎn)了個(gè)遍。“輪轉(zhuǎn)就是了解所有的疾病,不是頭疼醫(yī)頭、腳疼醫(yī)腳,要有一個(gè)全局觀。”丁倩解釋。
輪轉(zhuǎn)期間,丁倩從基礎(chǔ)開始。學(xué)習(xí)基本疾病、寫大病歷、問診患者、跟查房、跟手術(shù),學(xué)最基本的手術(shù)操作,打結(jié)、拆線。
“考試和實(shí)操完全不一樣,有時(shí)候縫合張力很大,回去以后莫名其妙就發(fā)現(xiàn)手指頭上都是傷口,后來才反應(yīng)過來是被胸科的10號(hào)線勒出來的。”丁倩對(duì)醫(yī)生真實(shí)的工作有了最直觀的認(rèn)識(shí)。
本科階段臨近結(jié)束,丁倩面臨專業(yè)選擇的問題。“有一次我的一個(gè)內(nèi)科老師跟患者家屬談話,談了一兩個(gè)小時(shí)!我是真的不行。”丁倩下定決心去外科系,丁倩找到時(shí)任唐都醫(yī)院麻醉科主任柴偉教授,申請(qǐng)做他的碩士,柴主任欣然同意。碩士結(jié)業(yè)前,丁倩以麻醉藥品的給藥方式為題做出優(yōu)秀的論文,順利畢業(yè)。
“本來想著工作,但當(dāng)年的分配情況不理想,索性就繼續(xù)考博。”丁倩考上博士,師從我國(guó)著名麻醉學(xué)專家熊利澤教授。博士期間的學(xué)習(xí)更加辛苦,丁倩開始接觸動(dòng)物模型等基礎(chǔ)實(shí)驗(yàn),“做實(shí)驗(yàn)”也成了丁倩博士期間一直連續(xù)不斷的的學(xué)習(xí)內(nèi)容。
“早上8點(diǎn)到實(shí)驗(yàn)室,晚上回來的早可能七八點(diǎn),晚的話要到12點(diǎn),博士三年期間除了每年過年會(huì)休息兩三天,剩下時(shí)間都在實(shí)驗(yàn)室。”除了上課時(shí)間,丁倩“釘”在了實(shí)驗(yàn)室。
丁倩做的是腦保護(hù),用麻醉藥給一個(gè)處理方式,再造模型,觀察能否產(chǎn)生腦保護(hù)的效果,還在基礎(chǔ)部做神經(jīng)生物試驗(yàn)。“傳統(tǒng)意義上動(dòng)物模型,造模、看現(xiàn)象、再看機(jī)制,其實(shí)很難。”丁倩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(shí)間和精力。
功夫不負(fù)有心人,丁倩博士期間做出了麻醉藥物對(duì)中樞神經(jīng)保護(hù)作用方面的機(jī)理研究文章,相關(guān)成果發(fā)表在業(yè)內(nèi)著名的《Anesthesiology》和《Anesthesia & Analgesia》雜志上。丁倩博士期間除了基礎(chǔ)實(shí)驗(yàn)工作,醫(yī)院的患者數(shù)量開始爆炸式增長(zhǎng),下科室支援臨床也成了常態(tài)。
“在軍校10年的學(xué)習(xí),過程真的很辛苦。但吃過這些苦后,在工作上你比別人更容易去覺得吃苦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”歷經(jīng)磨練,丁倩具備了超強(qiáng)的抗壓能力和吃苦耐勞的品質(zhì)。
02初聞不知曲中意 再聽已是曲中人
博士畢業(yè),丁倩以優(yōu)異成績(jī)留校,順利進(jìn)入已經(jīng)7年沒有留人的唐都醫(yī)院麻醉科工作。
“干活和干活是兩碼事,是否思考是關(guān)鍵。”丁倩始終堅(jiān)持著自己的邏輯性思維。
臨床學(xué)習(xí)之初,都是老師怎么說自己怎么做,藥品說明書每個(gè)字都認(rèn)識(shí),意思也知道;患者為什么現(xiàn)在是平穩(wěn)的?不平穩(wěn)的時(shí)候,按老師說的常用藥物處理也平穩(wěn)了,但是沒有深刻的理解,沒有優(yōu)化。
怎么樣還能讓患者更好?在正式工作之后,丁倩開始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重新學(xué)習(xí)。開始針對(duì)不同的患者,找出麻醉的注意要點(diǎn),設(shè)計(jì)麻醉方案,預(yù)演麻醉實(shí)施過程,逐漸做到融會(huì)貫通,形成自己的思考。
真正搞懂麻醉,是每一個(gè)操作,每一個(gè)目標(biāo)都要有理有據(jù)。當(dāng)外科醫(yī)生的要求和麻醉目標(biāo)不一致時(shí),麻醉醫(yī)生可以在保證患者平穩(wěn)同時(shí)在某一個(gè)范圍內(nèi),傾向于外科,讓手術(shù)順利進(jìn)行,但同時(shí)要明確告知外科醫(yī)生相關(guān)的風(fēng)險(xiǎn),外科醫(yī)生在得到麻醉意見后,也會(huì)根據(jù)患者情況來考慮調(diào)整手術(shù)方案或環(huán)節(jié),麻醉醫(yī)生也要明確提出需要外科醫(yī)生配合的工作。
知其然,知其所以然。丁倩認(rèn)為只有憑借自己的專業(yè)能力,和外科醫(yī)生形成有效溝通,才最有利于患者安全、手術(shù)安全、麻醉安全。
03麻醉錦旗頭一份
丁倩做二線醫(yī)生曾接診一位產(chǎn)后大出血的患者,患者外院前置胎盤,經(jīng)剖腹產(chǎn)取出胎兒后,無法止血。從急診科直接推到手術(shù)間,患者已經(jīng)氣管插管輔助呼吸,四肢四路輸血!情況緊急!丁倩接手后,一接心電圖,患者是200次/分鐘多室性心動(dòng)過速,雙側(cè)瞳孔散大固定。
“做監(jiān)護(hù)的同時(shí),我發(fā)現(xiàn)患者雖然已經(jīng)生產(chǎn),但整個(gè)腹部是膨隆的,就跟沒有生產(chǎn)一樣!趕緊就進(jìn)行有創(chuàng)動(dòng)脈監(jiān)測(cè),中心靜脈置管,麻醉后立刻開始手術(shù)。一開腹,就是4000毫升血,從腹腔直接出來,兩個(gè)桶就滿了。”丁倩當(dāng)時(shí)已經(jīng)懷孕6個(gè)月,顧不得許多,滿腦子想的都是保證麻醉安全以及萬一出現(xiàn)心臟停跳該如何應(yīng)對(duì)。
“外科醫(yī)生一邊做,一邊反復(fù)詢問,心跳停了沒?心跳停了沒?我就回答沒停,你繼續(xù)做。”丁倩全程密切關(guān)注著患者和手術(shù)進(jìn)程,維持循環(huán)穩(wěn)定,手術(shù)最終順利完成。患者返回ICU兩天后完全清醒,除子宮切除外基本恢復(fù)。
“我記得那個(gè)患者總共出了2萬毫升血,相當(dāng)于全身的血換了六七遍,居然那么快就恢復(fù)了!之后還碰到過兩三個(gè)類似產(chǎn)后大出血,大量換血,愈后良好。所以說這一類患者一定要積極搶救,有可能愈后很好!”丁倩觸動(dòng)頗深。

這也是丁倩第一次收到患者的錦旗。“以前麻醉從來沒有收過錦旗,我收的這個(gè)錦旗算是科室第一份,大家都很驚訝。”自稱“幕后工作者”的丁倩笑著說。
除了高危患者的麻醉處理,丁倩針對(duì)嬰幼兒麻醉也有深刻的理解。嬰幼兒生理和成人不一樣,很多器官還在生長(zhǎng)發(fā)育。比如心臟,成人能夠通過心肌收縮力增強(qiáng),加強(qiáng)心臟輸出量。但嬰幼兒不是這樣,心肌收縮力有限,不可能通過跳得有力增加泵血能力,只能靠頻率。新生兒如果達(dá)不到100的心率,就需要直接心肺復(fù)蘇了。此外,嬰幼兒耐受創(chuàng)傷差,全身血容量小。100ml的出血量對(duì)成人影響不大,如果是10公斤體重的兒童,全身只有800毫升血,這時(shí)就會(huì)很嚴(yán)重。對(duì)麻醉醫(yī)生來說是個(gè)挑戰(zhàn),有創(chuàng)操作、監(jiān)護(hù)等等,都要求更加精準(zhǔn)、精確,而且兒童麻醉藥品也比較少,藥物使用要求更高。
其次,嬰幼兒隨著年齡不斷變化,生理是不斷變化的,要求麻醉醫(yī)生熟悉每個(gè)年齡段兒童的生理。
04能力越大 責(zé)任越大
隨著工作能力的不斷提升,接觸到越來越多的麻醉患者,就像是不斷擴(kuò)大的圓的外接面也越來越大,丁倩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知識(shí)儲(chǔ)備需求也越來越廣泛。
來到西安國(guó)際醫(yī)學(xué)中心醫(yī)院麻醉手術(shù)中心任副主任,面對(duì)全新的環(huán)境和臨床同仁,如何有效配合?丁倩給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必須掌握更多的知識(shí)和新技術(shù),拿出客觀有效的依據(jù),從患者安全,麻醉安全角度給臨床醫(yī)生一個(gè)明確的建議,確保麻醉工作形成一個(gè)完整的閉環(huán)。
丁倩對(duì)每一臺(tái)手術(shù)的麻醉工作都是是從麻醉準(zhǔn)備開始的。提前同臨床醫(yī)師溝通,了解患者的情況、年齡、基礎(chǔ)疾病等。訪視患者及家屬,回顧所有的檢查、病史、用藥史、告訴患者如何配合麻醉工作,講解麻醉的注意事項(xiàng)。

很多患者是第一次進(jìn)手術(shù)室,多少會(huì)有一定的恐懼感。丁倩會(huì)告訴他們術(shù)前準(zhǔn)備,怎么吃藥、喝多少水、誰來接,接到什么地方,到了以后會(huì)有扎針和其他操作。針對(duì)重癥的患者,做動(dòng)脈穿刺時(shí)會(huì)告訴他這個(gè)會(huì)痛,需要配合。
蘇醒以后的情況丁倩也會(huì)提前告知患者,全麻患者氣管插管,蘇醒后會(huì)很難受。醒來以后要配合呼吸,不要去拔管,也不要使勁嗆咳,護(hù)士麻醉后導(dǎo)尿醒來可能會(huì)不舒服,需要患者配合。
除了跟患者溝通,丁倩還要跟患者家屬談話,告知普遍麻醉風(fēng)險(xiǎn),針對(duì)患者病情可能存在的特定風(fēng)險(xiǎn)等等,征得家屬同意確認(rèn)。
術(shù)前一天,丁倩會(huì)做好麻醉前各個(gè)方面的準(zhǔn)備。前期所有的準(zhǔn)備完成后,下一步才是術(shù)前麻醉實(shí)施階段。核對(duì)患者信息無誤,給藥過程中丁倩會(huì)不斷修正計(jì)劃。
“每個(gè)患者對(duì)麻醉藥物的反應(yīng)是不同的,差別會(huì)很大,一兩次給藥后,觀察患者反應(yīng)以及藥物代謝,才能確定患者的給藥規(guī)律。同時(shí)兼顧手術(shù)操作,創(chuàng)傷大時(shí),需要加大鎮(zhèn)痛,避免不良反應(yīng);沒有操作時(shí),調(diào)整為保持鎮(zhèn)靜和小量的鎮(zhèn)痛,始終提供一個(gè)穩(wěn)定的麻醉狀態(tài)。”丁倩解釋。
麻醉的第三個(gè)階段是蘇醒期,患者手術(shù)結(jié)束需要蘇醒并恢復(fù)到一定的生理狀態(tài)。麻醉后給予鎮(zhèn)痛,應(yīng)對(duì)手術(shù)帶來的創(chuàng)傷問題。針對(duì)術(shù)后拔管的患者,還需要控制呼吸恢復(fù)過程中心率,血壓水平,維持循環(huán)穩(wěn)定。

全麻的患者術(shù)后會(huì)到麻醉恢復(fù)室,再觀察一段時(shí)間,看看麻醉藥物是否完全代謝。在術(shù)中高刺激的情況下,患者表現(xiàn)和術(shù)后無刺激時(shí)候是不一樣的,有可能會(huì)發(fā)生再抑制,或者是鎮(zhèn)痛泵的給藥和之前體內(nèi)的藥物混合后也可能發(fā)生抑制。通過在恢復(fù)室觀察還可能發(fā)現(xiàn)其他問題,比如出血問題,發(fā)現(xiàn)循環(huán)不穩(wěn)定,引流出血量比較大時(shí),就可以及時(shí)糾正。
確認(rèn)患者沒有問題,就可以送回病房了,但丁倩的工作仍然沒有結(jié)束。返回病房并不意味患者體內(nèi)的麻醉藥物完全代謝。丁倩會(huì)跟病房交班,告知患者主管醫(yī)生需要注意的事項(xiàng)。比如術(shù)中發(fā)現(xiàn)血鉀問題,補(bǔ)鉀的濃度、速度要求,術(shù)中補(bǔ)了多少,術(shù)后在病房還需要補(bǔ)多少;或是麻醉給藥過后可能出現(xiàn)的心率減慢問題,如果患者在病房出現(xiàn)類似問題,主管醫(yī)生知道原因,可以對(duì)癥處理。
給護(hù)士交代護(hù)理注意事項(xiàng),給家屬交代怎么看監(jiān)護(hù)儀,哪些是最重要的部分,出現(xiàn)什么情況要第一時(shí)間呼叫護(hù)士,教家屬怎么用鎮(zhèn)痛泵,以上所有工作結(jié)束,麻醉工作才算告一段落。如果患者后續(xù)出現(xiàn)緊急情況,丁倩也會(huì)到場(chǎng)協(xié)助臨床科室解決問題。
麻醉如何給臨床提供更好的服務(wù)?丁倩一直在思考這個(gè)問題。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,首先就是不斷的提高麻醉水平,同時(shí)要與臨床形成有效溝通,關(guān)注術(shù)中操作是否足夠輕柔,是否足夠無血化,不斷加強(qiáng)和臨床的配合度。
05麻醉未來的無限可能
很多八九十歲的高齡患者,心肺功能差,本身風(fēng)險(xiǎn)就大,麻醉藥品是讓患者從清醒到鎮(zhèn)靜鎮(zhèn)痛狀態(tài),從而耐受手術(shù)的創(chuàng)傷和刺激,對(duì)患者又是一種負(fù)荷。
丁倩認(rèn)為這是所有麻醉醫(yī)生都會(huì)面臨的風(fēng)險(xiǎn),必須承擔(dān),但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合理的降低麻醉風(fēng)險(xiǎn)。
首先評(píng)估手術(shù)是不是一定要做,立馬要做。如果沒有時(shí)間讓患者情況改善,例如主動(dòng)脈夾層破裂,一定是越早做越好。
第二就是持續(xù)不斷的學(xué)習(xí)。學(xué)習(xí)最新的藥,最新的技術(shù),外科手術(shù)的進(jìn)步。
麻醉藥種類越來越多,麻醉醫(yī)生要熟悉不同藥品的作用時(shí)間、起效時(shí)間、代謝、對(duì)循環(huán)的抑制情況,針對(duì)不同患者,制定出最優(yōu)方案。例如鎮(zhèn)痛類藥物,分長(zhǎng)效、短效、對(duì)呼吸抑制小的、針對(duì)內(nèi)臟神經(jīng)痛的、針對(duì)銳性疼痛性刺激的。藥品用法麻醉醫(yī)生要“如數(shù)家珍”。
麻醉工具越來越多
以前的穿刺都是盲探性的,后來有了神經(jīng)刺激引導(dǎo)、超聲引導(dǎo),讓麻醉可視化、創(chuàng)傷更小。還有可視的插管技術(shù),以前氣管插管來控制呼吸,現(xiàn)在還有喉罩,種類也多種多樣,還能作為工具控制呼吸、參與搶救。工具使用麻醉醫(yī)生要“手到擒來”。
麻醉理念越來越新
要求更加關(guān)懷患者,關(guān)注心理學(xué)影響;加快康復(fù),以前長(zhǎng)時(shí)間的禁食禁水,現(xiàn)在可以明確不同食物或是飲料的禁飲食時(shí)間,避免患者長(zhǎng)時(shí)間的術(shù)前等待消耗,減少術(shù)中快速、大量補(bǔ)液加重心肺負(fù)荷,降低圍術(shù)期管理難度。理念應(yīng)用麻醉醫(yī)生要“溫故知新”。
探索麻醉學(xué)科前景
“就是轉(zhuǎn)變一個(gè)思路,患者全程由麻醉或者重癥來進(jìn)行管理,適合手術(shù)時(shí),請(qǐng)外科來會(huì)診,手術(shù),術(shù)后由我們繼續(xù)管理患者,保障患者。”丁倩如是說。